郎琳:中英携手,共育创新

文/夏敏
对于“中国是模仿者还是创新者”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郎琳(Grace Lang)有着精辟见解。她说,这两个角色“不一定互相排斥”。作为英国研究和创新机构(UKRI)中国区主任,她对此很了解。UKRI是一家英国国家基金资助机构,顾名思义,投资研究和创新。中国办公室是UKRI的四个海外办公室之一,郎琳在这里领导着一个团队,过去11年来已经促成近三亿英镑的联合投资,为近70个联合研究和创新项目提供支持,涉及中英两国200多所大学、众多研究机构和130家企业。
她说:“中国正在迅速发展,规模错综复杂,无法简单地以‘创新者’或‘模仿者’来全面概括,评估创新能力很复杂。”最近,在接受《TheLINK》采访时,她谈到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的价值,以及中国在渐进性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她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种方式都有着“重要作用和价值”。“突破性创新给企业或整个行业带来巨大影响,而渐进性创新给某种服务或产品带来小的改变。这是两种战略性创新方式,在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互为补充。采用哪种方式通常取决于公司或个人在承担风险方面的态度。”她解释道。
她补充道:“有很多例子显示,中国非常擅长渐进性创新。在一些领域,中国有着深刻的技术知识,让他们能够迅速采用现有技术满足市场上的新需求。包括突破性创新在内的再平衡过程需要时间和坚实的知识基础。根据过去15年我在研发投资方面的工作经验,中国的转变着实激动人心,我确信未来几年的变化将会更加令人惊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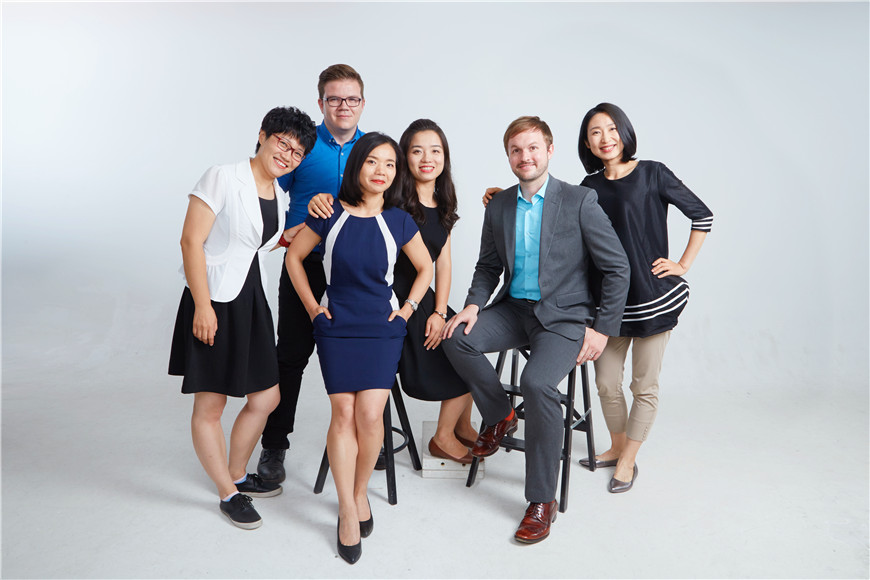 郎琳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作为UKRI中国区主任,她会花很多时间调查中国最新的研究和创新趋势,甄选中英两国能够通过强强携手或优势互补来增加价值的潜在机会和领域。她解释道:“研究和创新是中英关系的核心要素。英国是中国的第二大科技论文合作撰写伙伴。”关于与中国合作研究和创新的战略机会,她领导的团队也会向英国总部提供意见和建议。他们还致力于与中国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机构建立并加强联系,协商高质量的联合资助研究和创新计划,提升投资价值以实现科研、经济和社会影响力。
郎琳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作为UKRI中国区主任,她会花很多时间调查中国最新的研究和创新趋势,甄选中英两国能够通过强强携手或优势互补来增加价值的潜在机会和领域。她解释道:“研究和创新是中英关系的核心要素。英国是中国的第二大科技论文合作撰写伙伴。”关于与中国合作研究和创新的战略机会,她领导的团队也会向英国总部提供意见和建议。他们还致力于与中国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机构建立并加强联系,协商高质量的联合资助研究和创新计划,提升投资价值以实现科研、经济和社会影响力。
郎琳于2008年加入现在供职的机构,并帮助该机构从独立的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中国发展成为UKRI中国,UKRI包括四个海外办公室和英国总部,UKRI中国是其中重要一员。她于2016年参加中欧EMBA课程,希望通过理论学习商业技能为职业生涯增添动力,她如愿以偿。
阅读以下访谈,了解郎琳在培养创新以及增进中国与欧洲关系方面所做的贡献。
《TheLINK》:能否介绍一下UKRI以及你的工作?
UKRI每年的预算超过60亿英镑,通过七家研究委员会、创新英国(Innovate UK)和研究英国(Research England)资助研究和创新。UKRI有四个海外办公室,分别位于北京(UKRI中国)、布鲁塞尔(UKRO)、新德里(UKRI印度)和华盛顿(UKRI美国)。
我管理的UKRI中国成立于2007年9月(当时名为RCUK中国,2018年4月更名为UKRI中国)。
在我担任RCUK中国副主任期间,我们发起了第一个与中国联合资助的研究项目(2008年),这是建立中英研究和创新合作关系的一个里程碑。
2014年我晋升为RCUK中国主任,2018年担任UKRI中国主任,2008-2014年,我们每年用于联合资助的资金约为1000-1500万英镑。自2014年起,这个数字已经翻番。我们不再只是联合资助研究项目,也开始设计企业主导的项目。2014年我们与科技部联合发起了一个关于可持续制造的联合项目,以企业为主导合作伙伴。后来,UKRI下属机构创新英国与地方科技委员会合作,在江苏、上海和广东联合资助了多个项目,支持新兴高科技行业的研发。
现在,我花很多时间调查中国最新的研究和创新趋势,甄选中英两国能够通过强强携手或优势互补来增加价值的潜在机会和领域。我也花了很多时间与国内以及其他海外办公室的同事交流,了解英国和其他地区在研究上面临的最新挑战。这有助于思考我们如何团结不同国家的公共投资者,解决共同面临的挑战。我还参加学术研讨会和公共活动,与研究人员、创新者和企业家交流,了解他们从哪里获益,在哪方面遇到障碍,以及我们能够提供哪些切实的帮助以促进合作顺利进行。
 《TheLINK》:你的头衔中包含创新这个词,这是当下的一个流行词。对你个人来说,在当前职位上具备创新精神有多重要?
《TheLINK》:你的头衔中包含创新这个词,这是当下的一个流行词。对你个人来说,在当前职位上具备创新精神有多重要?
在一个主要资助研究和创新的组织中,很难不具备创新精神。UKRI是一个在英国新成立的组织。把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s)、创新英国(Innovate UK)和研究英国(Research England)结合起来成立这样一个组织,通过与个体以及集体合作,为研究和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支持,这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创新方式。
我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与国内同事以及不同国家的资助伙伴合作,开发多样化的资助机制,回应研发领域的迅速变化以及新兴研发群体的需求。从我们的投资组合中你会发现,过去十年我们的投资涵盖很多领域,包括能源、农业和食品安全、老龄化和健康、创意产业、制造业和环境等。我们的资助机制也多种多样,包括对大量研发项目提供网络和资金支持、联合研发中心、合作机构和行业特定加速器。设计量身定制的资助机制以满足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而且这些不同的学术和商业领域包含非常多的创新思维。
在我的工作中,最难的是管理非常多的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来平衡并实现组织目标。这包括与不同国家的公众研发投资机构建立信任关系,打造伙伴关系,促进学术界与各种行业之间的知识交流,更好地整合研究和创新。
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建立信任,这是我们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领导力课程中学到的核心内容。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真正需求,才能获得信任。学会从他人角度看待和领会事物有助于找到共同的基础,找出适合所有人的解决方案。要让政府决策者、学术界和商界结合起来,你需要了解这些不同群体所用的语言。在新兴高科技领域促进跨界合作伙伴关系需要掌握宏观经济、供应链管理、并购等学科的相关知识。课堂上的分享和辩论让我获益,令我深思。
《TheLINK》:你提到中欧EMBA如何帮助你克服目前在工作中遇到的挑战,请问你最初入学是出于什么原因?当时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现在都实现了吗?
2016年我加入中欧EMBA时,我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商业思维”和发展在私营领域的人脉网络来拓宽视野。我已经实现这个目标,并且还有更多收获,通过与同学和校友网络的互动,我对不同的行业有了深入了解。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有着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合适群体。无论身处何地,中欧都把我们连接在一起,通过EMBA课程构建的支持网络会让我们走得更远。
 《TheLINK》:你在中欧EMBA学到的最有用的课程是什么?
《TheLINK》:你在中欧EMBA学到的最有用的课程是什么?
开发积极思维并通过展示可能性与他人进行分享。安德烈·威尔茨玛(Andre Wierdsma)教授告诉过我们《国家地理杂志》记者德威特·琼斯(Dewitt Jones)的一句话,特别鼓舞人心,他说,“通过庆祝正确的事情,我们找到改正错误的能量。”在把工作从优秀做到卓越的过程中,积极性至关重要。
另外,在中欧EMBA课堂上,同一门课程基本上都由中外教授共同授课,这也让我受益良多。我发现,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还选了两门全英文授课的选修课,让我有机会与Global EMBA的同学交流。看到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互相探讨商业问题,这种体验非常棒。我非常喜欢中欧的一点是,你能同时接触到本土和全球人脉网络。
如果KPI是基于来到中欧之前和之后填补的商业知识空白,以及为我所在机构做出更大的战略性贡献,那我肯定是优等生!如果KPI是创建自己的企业,提高企业的估值,或者让你的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我离优等生还差很远。但是我的一些同学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两年的中欧EMBA学习生涯给我带来了愉快的体验。虽然在准备毕业考试的时候有压力,但整个体验非常有趣。每次看到我们班在台上表演京剧和音乐剧、穿越戈壁沙漠、盛装出席新年庆典的视频,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我知道,在中欧的两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是一段不断超越自己和丰富人生阅历的经历,这毋庸置疑。
《TheLINK》:像你一样的专业人士或是其他商业人士如何增进中英或中欧关系,你能给出三点建议吗?
开放思想,并且愿意学习、领会,能够灵活变通;
打造一个多样化的团队和一个跨行业的支持网络;
竞争让我们变得更快,但合作让我们变得更好。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都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的时候,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建立互惠互利的共识,并且求同存异,这非常重要。正是多样性让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充满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