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磋商!为什么说中美“斗则俱伤”?
9月5日,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牵头人进行通话,双方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双方一致认为,应共同努力,采取实际行动,为磋商创造良好条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芮博澜(Bala Ramasamy)教授的研究表明,中美对彼此的市场依存度较高,在中短期甚至长期内,没有一个国家可取代中美在彼此市场中的地位。因此,双方之间展开冷静谈判,是解决目前僵局的唯一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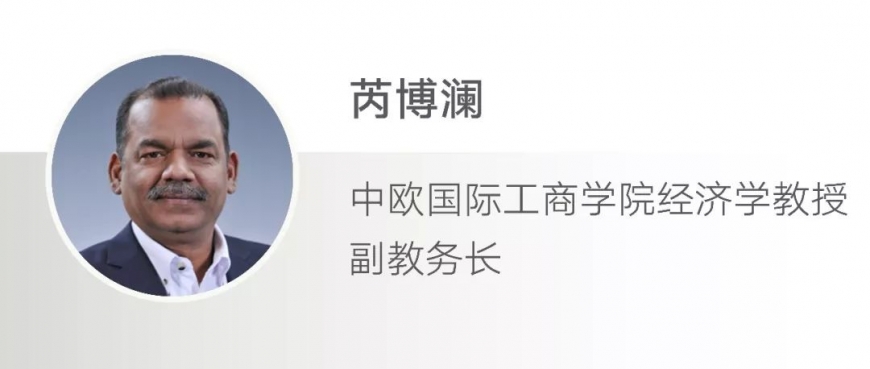
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但双方谁也不会赢得这场争端,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满足美国市场对产品的巨大需求。即使在理想状态下,其他任何国家的产能也暂时无法企及中国的水平,因此最终美国将别无选择,而不得不继续购买中国的产品。
同样,其他任何国家的需求与美国的需求相比也存在巨大的差距,这就意味着短期内中国市场其他国家的顾客并不能取代美国顾客的消费量。
我们的研究发现或可为缓解近期中美双方的紧张态势打下一个基础。
2019年8月2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发了条推特:“我们不需要中国……”,并敦促美国企业迁出中国,落脚他处,或者直接把工厂迁回美国。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时断时续的关税战大大增加了消费者和企业的不确定性,并对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发起的一项调研显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消费者更愿意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花出去。2019年上半年,进入中国的绿地投资项目同比减少了30%有余。那么,对中国来说,对美出口有多重要?简而言之,中国需要美国吗?
2018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价值约为4770亿美元,占总产值的3.7%左右(以名义GDP计算)。这一金额在中国意味着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尽管对美出口商品中有一大部分是进口商品(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的零部件)而非中国制造,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量中国对美出口商品都是经由香港特区转口到美国,因此这部分商品会计入香港出口,而非中国大陆出口。

设立关税的初衷是削减从贸易伙伴国家的进口,而并非彻底消除进口。关税上调造成的价格上涨会迫使零售商和消费者去寻找替代品——来自其他国家的或国产的商品(如果存在的话)。有经济学家指出,长期来看,美国的所谓进口需求弹性约为-1.55。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30%,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将减少约46.5%或约2200亿美元。
即使有可能找到另一个进口来源国,是否有国家能完全取代中国的产能?举个例子,美国从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商品是手机。2017年和2018年,仅手机就占美国从中国进口额的13%左右,即每年约700亿美元。2017年,中国向全球出口了价值约1680亿美元的手机。备受关注的中国潜在替代国——越南,其手机出口总额约为300亿美元,而美国的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约为320亿美元。这意味着,即使越南将其所有出口的手机出口到美国,同时美国收回其所有出口的手机来服务本土市场,仍然无法完全取代中国的产能从而满足美国本土市场的需求。
再看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另一种商品:鞋类。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约143亿美元的鞋类(约占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2.7%),或约16亿双鞋。只有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土耳其将所有出口的鞋子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到美国,才能取代中国的产能。这些例子表明,其他国家取代中国作为美国主要进口来源是不现实的,至少在中短期内是这样的。因此,中国厂商大可放心,他们有好几年时间用来重新配置出口,以应对关税对其业务的影响。

那么,其他国家又可在多大程度上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商品的出口目的地呢?根据2018年的进口数据,大约需要9个国家加起来才够。只有荷兰、英国、德国、印度、瑞典和法国停止从世界所有其他地方进口手机,转而从中国进口,其进口量才大致等同于中国对美国的手机出口量。相较而言,如果英德两国选择从中国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进口所有鞋类,其进口量才等同于中国对美国的所有鞋类出口量。
为了进一步评估中国为其商品寻找其他买家的潜力,我们研究了大量商品类别,并计算了各国的进口相似度指数,对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与其他国家从中国的进口(从世界的进口减去从中国的进口)进行了比较。指数100意味着一个国家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完全相同,而0意味着该国未进口任何一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因此,指数较高,就表示该国越可能成为取代美国的中国商品出口目的地。
在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我们研究了各个不同的商品类别,其中包括消费品和资本品。我们选取了占中国对美出口80%份额的共计238种商品作为研究对象。由此得出的进口相似度指数最低的为瑞士的12, 最高的为印度的88。 与此同时,我们还考虑了特定国家的进口能力。将指数与进口规模相乘(中国除外)后,我们得出了一份国家清单。这些国家是可以取代美国的中国最佳出口目的地。位居前列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德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分列第六和第七。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印度跻身其中。

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首先,美中贸易关系根深蒂固。一个是极其庞大且永不满足的市场,而另一个是运行顺畅的生产机器。在中短期内,甚至可能在长期内,都不会有任何国家可以取代这种关系。双方之间“冷静”的谈判确实是解决目前僵局的唯一途径,而针锋相对的处理方式对双方都有害无利。
其次,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因为欧盟是唯一与美国需求相当的可行的替代地区。无论西欧还是东欧,在我们的分析中都占据重要位置。这就意味着在英国脱欧时,和英国谈一桩“大”生意符合中国的利益。
第三,继续发展国内现有市场并开拓新市场,从而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这对中国企业来说绝对是个好主意。
芮博澜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杨志熙任教于香港公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