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EO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
“CEO是公司里最‘无知’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像讽刺,却道破了组织管理的残酷现实。不久前,小鹏汽车CEO何小鹏在某媒体专访中亲述了曾经“被公司供应链下属合伙瞒骗”的惨痛经历,并坦言“一个公司的CEO有时候是最晚知道真相的”。为什么CEO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与国际商务副教授蔡舒恒从管理学角度,拆解了“皇帝新衣”的困局,并提出破解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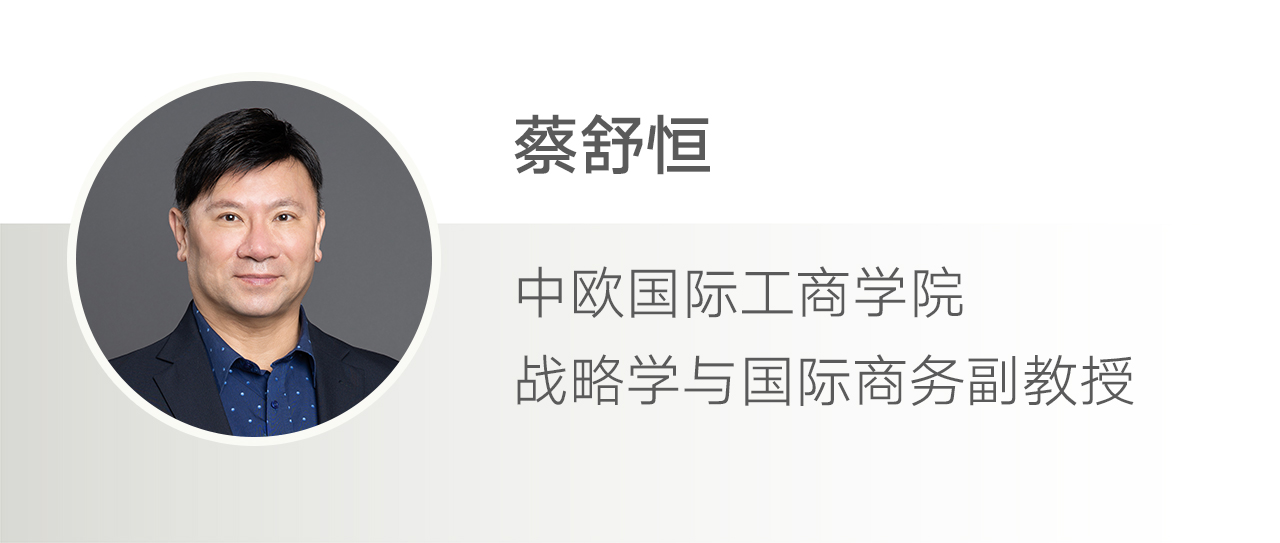
2015年,大众汽车“排放门”震惊全球——工程师在柴油车上安装作弊软件,瞒过管理层长达7年。直到美国环保署介入,CEO文德恩才在记者会上茫然地说:“我也是刚知道。”
这不是孤例。从富国银行的虚假账户,到波音737MAX的致命缺陷,无数案例证明:CEO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为什么站在公司金字塔尖的人反而最容易被蒙蔽?如果连CEO都被骗,公司还有真相吗?
在中国历史上,君昏臣蔽的案例也比比皆是。秦朝赵高在朝堂上指鹿为马,群臣畏惧权势纷纷附和,秦二世胡亥终被蒙蔽;明朝嘉靖皇帝二十余年不上朝,仅靠严嵩的“青词”(道教奏章)治国,直到海瑞上奏《治安疏》痛陈时弊,才惊觉国家早已危机四伏……这些故事堪称古代版的“CEO困境”,可见这个问题早已困扰人类上千年之久。
从一个恪尽职守的CEO角度,即使理想很丰满——组建高素质的团队成员、制定完善的汇报流程甚至经常下基层走访……但现实往往是“骨感”的:团队默契有时会变成“默契的沉默”,完美的流程可能会过滤掉关键的真实声音,基层走访看到的可能也是精心准备的“样板戏”……
明镜何以蒙尘?好的CEO为何也会中招?这不是简单的欺骗,也无关道德或能力问题,而是组织运作中难以避免的系统问题。
01
委托代理陷阱
委托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根据这一理论,任何组织均可视为由委托人和代理人组成的网络。在这种关系中,委托人(如股东)委托代理人(如CEO)代表其行事。CEO又通过管理层将执行权委托给各级员工。在公司层面,CEO本身虽为高级代理人,但他们也依赖于公司内部其他员工——他们的下属,这些下属在此关系中扮演新的代理人角色。理论上,每个层级的代理人都应该忠实追求委托人的最佳利益,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首先,代理人天然掌握着委托人难以获取的操作细节,这种信息优势往往导致关键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选择性过滤。当下属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不向CEO完全透露真实情况时,就可能导致CEO对企业的整体状况和外部环境的误解。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下属可能认为隐藏信息可以避免短期内的冲突或不利后果,而长期来看,这种行为可能损害企业的整体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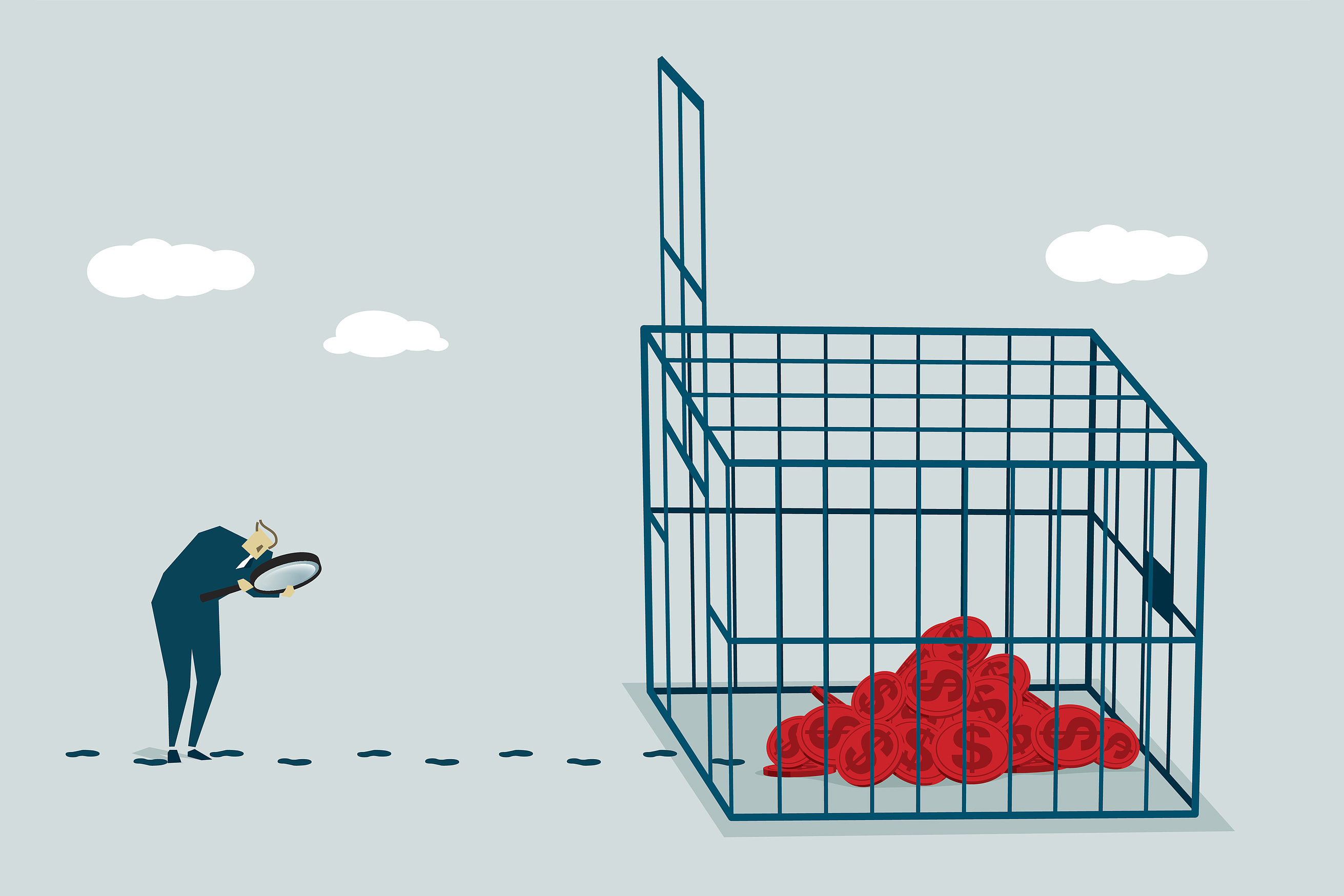
其次,激励目标不一致引发的行为偏差。股东追求长期价值,管理层关注短期业绩,董事会重视战略发展,执行层在意个人考核指标。这种根本性的目标错位,使各层级代理人的决策与组织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当“完成季度目标”比“坚守合规底线”能带来更直接的回报时,隐瞒信息甚至欺骗行为就会成为员工的理性选择。
最后,当信息不对称与激励不相容相互强化,就形成了道德风险的乘数效应。代理人既掌握信息优势,又面临扭曲的激励结构,最终导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被系统性地合理化。这种双重困境使得组织中的信息失真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制度设计缺陷的必然结果。
大众汽车的“排放门”便是这一困局的典型写照。工程师们并非天生欺诈,但在达标奖励、违规严惩的考核体系下,他们理性地选择了作弊软件这条路径——因为对代理人而言,保住饭碗远比环保承诺更现实。初级员工发现隐患却担心影响团队绩效,中层管理者知情却顾虑职业发展,最终导致高层领导被完全蒙蔽。这场持续七年的集体沉默,直到美国环保署用第三方检测才被捅破,恰恰印证了代理理论的核心命题:当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时,隐瞒将成为组织的常态。
02
信息传递失真
在组织中,信息传递的准确性是影响决策质量的关键因素。CEO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者,理论上应该是获取全面信息的中心节点。然而,实际情况是,CEO通常是最后一个了解到组织内部真实情况的人。
在理想状态下,信息应该是自由流动的。但在现实中,组织中的信息传递几乎从不直接,也不透明。它往往是一个逐级上传、层层过滤与主观加工的过程。正如管理学大师詹姆斯·马奇与赫伯特·西蒙在其著作《组织》中指出的那样:组织成员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会基于自身的有限理性对信息进行简化与筛选,导致上层决策者获取的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有误导性的。
组织的层级结构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扭曲的问题。在多层级的组织结构中,信息需要通过多个中间层才能传递到CEO。每经过一层,信息都有可能被进一步筛选或修改。层级越多,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大多数传统企业中,组织结构呈典型的金字塔形。CEO处于最顶层,而信息则需要从最基层一级级上传。每一层都可能成为“信息过滤器”或“失真器”。管理学者亨利·明茨伯格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中对组织结构进行了系统分类,并指出在典型的“机器型官僚结构”中,信息必须按照层级传递,这种结构虽然有助于流程规范,但也极易导致沟通迟缓与信息失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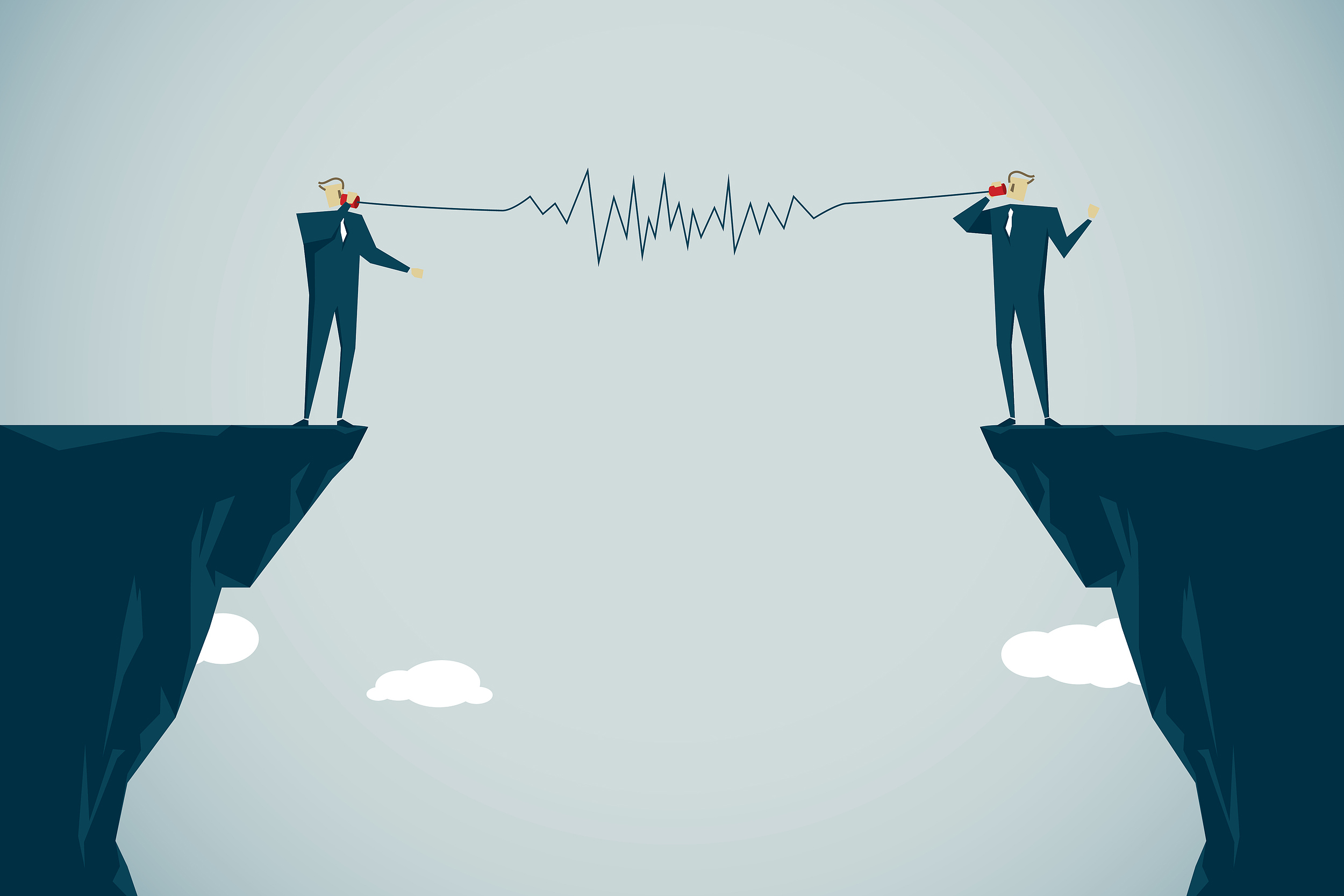
此外,信息在层层传递的过程中,还会经历一次次“语言转译”。中层管理者往往会将实际情况“翻译”为高管易于理解的形式——KPI、报表、图表、指标等。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大大削弱。当信息最终抵达CEO时,它已经不是原始事件或问题的真实反映,而是被多次编码后“抽象数据点”。CEO看到的是结果,而非过程;是数字,而非脉络。
更复杂的是,信息不仅在形式上被简化,在内容上也被“立场化”。不同的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同一问题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解读。销售部门可能淡化客户投诉,强调市场潜力;技术部门可能强调系统安全,弱化进度问题;财务部门则可能加强成本控制,忽略运营困难。最终,CEO所看到的信息,很可能只是多个部门博弈之后的“折中版本”,而非实际问题的本来面貌。
波音737MAX的飞控系统MCAS(机动特性增强系统)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导致多起空难。然而,在事故发生之前,公司的高层并未充分掌握这些风险信息。原因何在?波音的组织层级复杂,前线工程师与高层之间的沟通存在严重断层。中间管理层未能,也可能不愿将问题上报。CEO直到事故发生后,才真正全面了解问题的严重性。这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典型的组织信息传递失败的案例。
在组织中,信息不是自然流动的水。当信息被层层过滤、扭曲甚至掩盖时,再强大的CEO也只能在“事后”才明白真相。如果一个组织不能正视信息传递的结构性问题,CEO永远也无法真正“掌握全局”。
03
心理安全赤字
组织文化是企业“看不见的手”,它塑造着员工每天的行为方式、沟通模式与价值判断。在许多企业中,强调服从、追求绩效、回避冲突的文化氛围主导一切。在这种文化中,员工并不总是敢于说出他们所知道的问题。即便他们意识到某个流程存在风险、某项决策方向错误,他们也往往选择沉默。
这种现象并非因为个体懦弱,而是组织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只报喜不报忧”的文化规范。即使CEO鼓励“开放沟通”,员工也未必真的相信发声是安全的。表面上的“沟通渠道畅通”,掩盖的是更深层的“组织沉默”——一种系统性的不说、不问、不传达。
那么,员工为何选择沉默?关键在于组织文化对个体行为选择的作用——这就引出了“心理安全”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艾米·埃德蒙森提出的心理安全概念指出:心理安全是指个体在团队中感到可以毫无畏惧地表达真实观点、承认错误、提出质疑,而不会因此受到羞辱、排斥或惩罚。
当心理安全缺失时,员工即便知道问题存在,也不愿冒险说出真相。他们担心“说错话”会被认为不忠诚或不专业。在等级制度森严或高压绩效文化下,这种恐惧尤为明显。于是,信息在尚未发出前就已被“自我审查”,真相在基层员工心中悄然沉没,CEO便自然被蒙在鼓里。
可以说,组织文化是外在氛围,心理安全是内在感受。当一个组织缺乏包容、容错与倾听的文化基础时,员工的心理安全便难以建立,甚至不断被侵蚀。即便制度上设置了“建议箱”“匿名反馈”或“透明汇报机制”,如果员工内心并不相信“说真话是安全的”,这些制度最终也只是形式主义的摆设,无法真正激发坦诚沟通。因此,员工的沉默往往不是出于无知或者冷漠,而是出于恐惧感与不信任。这不是信息缺失,而是信任断裂。

真相不是不可知,而是无人敢讲。这种“组织沉默”比信息失真更危险,因为它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让高层误以为“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从而在战略判断中走向盲区。
富国银行的虚假账户丑闻便是组织集体沉默、心理安全缺少的典型后果。为了完成不切实际的销售指标,大量员工在数年间为客户擅自开设虚假账户,仅为达成所谓的“交叉销售”目标。事实上,早有员工意识到这一行为的风险,甚至试图向管理层发出警告。但在一个高度绩效导向、惩罚制度严格、缺乏心理安全的组织文化中,这些声音非但未被重视,反而被迅速压制。许多员工事后坦言,他们不敢质疑目标设定,更担心被视为“不够进取”或“业绩不佳”,从而面临被降职或解雇的风险。最终,问题在组织内部沉默多年,直到媒体曝光和监管调查,才公之于众。
因此,信息过滤的现象,表面上是结构问题,实则是文化问题。表面上看是信息逐级上传,实质是“逐级揣摩”与“逐层审查”。每一个层级都在“加工”信息——不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事实,而是为了更安全地迎合上级偏好。这不是个体的道德滑坡,而是组织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一种“生存智慧”。最终抵达CEO面前的,不再是真实信息,而是一份符合上级期待、迎合组织倾向、偏离事实本身的“定制信息”。
组织中这种“表面民主、唯上是从”的文化,正是信息扭曲的深层动因。如果组织不去正视这种“文化性失真”,再好的制度、再快的流程、再多的数据,也无法让CEO真正看见真相。
04
破解之道
要破解这一组织顽疾,必须跳出个体失察的视角,从系统层面重新思考信息为何无法有效上达。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高管是否勤于走访,也不在于团队是否忠诚尽责,而在于组织是否允许真相流通。
首先,正如代理理论所揭示,组织中的每一位员工,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代理人”。而代理人之所以选择隐瞒,往往源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当短期KPI压倒一切,当“报喜”比“报忧”更有回报,沉默与粉饰就成了员工的理性选择。
组织要改变这一逻辑,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激励制度:将长期主义写入绩效体系,将发现问题、揭示风险纳入正向激励。代理人只有在个人收益与组织利益高度一致时,才有动力成为“吹哨人”而非“掩盖者”。
其次,组织结构本身需要改变信息流动的方式。如果CEO只能依赖传统单一的信息渠道,那么他所看到的就只能是被修饰过的现实。因此,组织必须打破这种单向、垂直的信息汇报逻辑,建立多元的信息回路,让真相有更多元的出口,让CEO能够直接聆听来自一线的原始声音。
然而,真正决定一个组织中能否听到真话的,仍然是组织文化底层的价值观。制度可以设计,流程可以优化。但员工是否敢说真话,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感受到“心理安全”。当一个组织默许甚至鼓励“溜须拍马”、强化对“上级喜好”的揣摩与迎合,员工自然会将“说真话”视为一种高风险行为。
只有当员工相信,说出真相不会被羞辱、被排斥、被惩罚,他们才有可能开口。心理安全不是靠口号塑造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组织实践中逐步建立的。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承认自己的无知与错误,公开接纳“难听的声音”,持续传递一个信号:问题不是威胁,而是改进的起点。只有当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表达不同意见不会带来负面后果时,真相才会被说出来,信息才会自由流动。组织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敢讲真话、能听真话、愿改真错的地方。

今天的组织还迎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外部助力”——人工智能。AI技术正悄然改变着信息流动的方式,也为破解“CEO信息盲区”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传统组织中,信息的获取与上报高度依赖人工判断与人际网络,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意识、层级结构和利益博弈的影响。而AI的介入正在打破这一逻辑。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行为分析、情绪识别等技术,AI可以在不依赖层级中介的前提下,从庞杂的数据流中自动识别出异常信号与潜在风险。
例如,员工在内部系统中频繁搜索某一类条款、客户在社交媒体上反复表达某种不满、团队协作平台中出现非典型沟通模式——这些原本被忽略的信息,在AI的扫描下可以浮出水面,为管理层提供前所未有的“组织感知能力”。
当然,AI不是万能的,数据不会自动变成洞察,它无法替代领导者的判断与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AI的出现,正在不断推动组织重新思考信息应该如何运转,并为CEO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而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技术是否足够先进,而在于组织是否愿意用它来暴露真相。AI可以成为CEO的“第二双眼睛”,但前提是这位CEO真心想看见那些不那么好看的部分。关键也在于他是否愿意打造一个既支持人性表达,又拥抱技术洞察的组织生态。
CEO不可能成为“无所不知”的人,但他可以成为那个“拥抱真相”的人。他不需要掌握所有的细节,但必须确保,在关键时刻,那些最不愿被听见的声音,有机会被听见。
领导力的本质,不是完全掌控信息,而是创造一个让真相浮现的环境。真正成熟的组织,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能够被及时发现,被诚实面对,被集体修复。
本文作者系蔡舒恒(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与国际商务副教授)、张云路(西交利物浦大学)、张文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