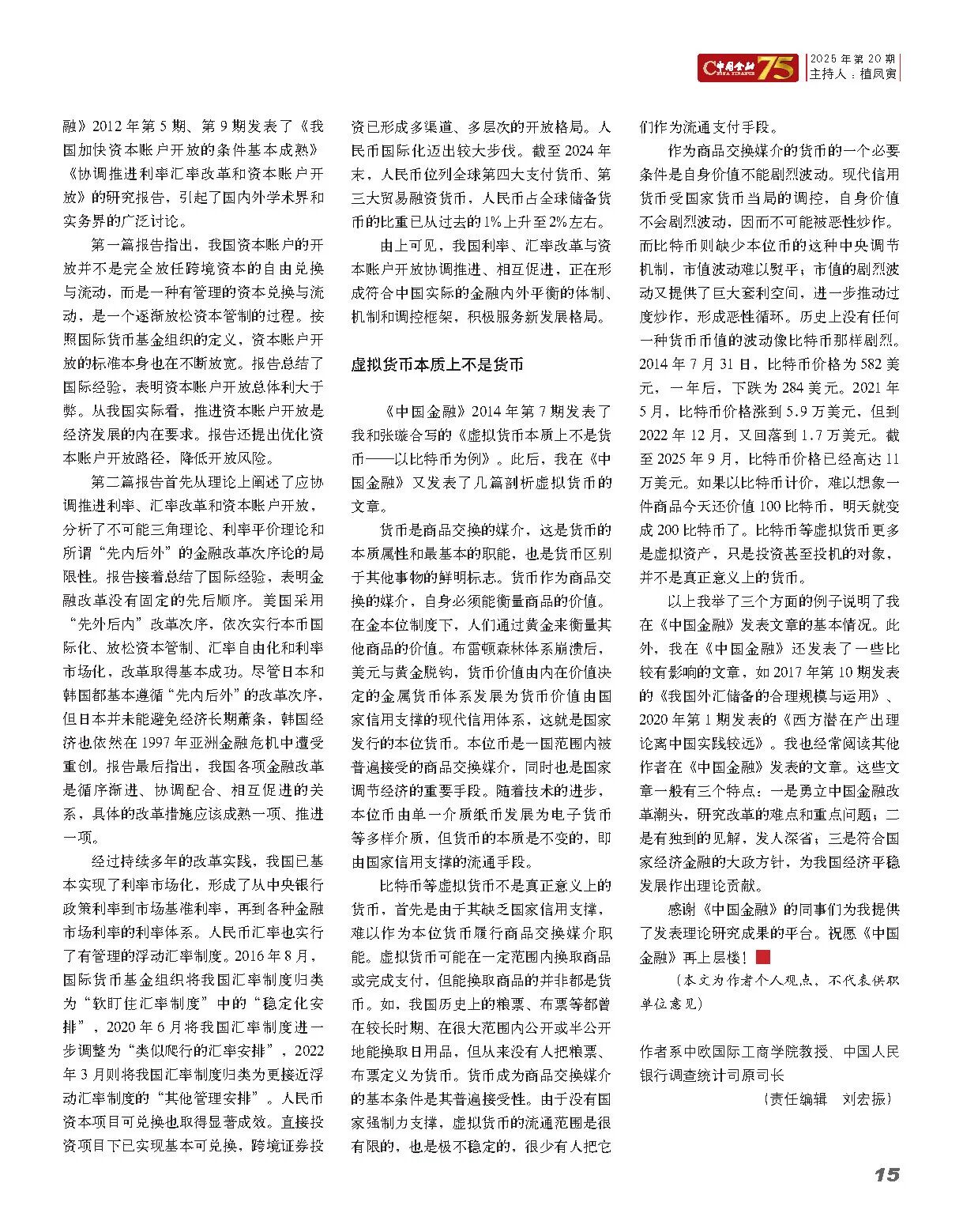盛松成:《中国金融》为我铺筑了创新研究之路
自2002年迄今的20多年中,我在《中国金融》发表了30多篇文章。回顾这些文章的内容和写作、发表经历,思绪联翩。这些文章涉及的面比较广,我想举几个主要方面的例子,回溯我参与当时中国金融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独创的指标
社会融资规模(以下简称社融)是我国独创的金融宏观监测与调控指标。社融的创立是一项“从0到1”的工作,是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领导指导和鼓励下,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在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我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和牵头人。从社融概念的提出、社融增量指标到存量指标的确立、社融全国数据至分省数据的统计和发布,历时整整五年。自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以来,该指标迄今已连续15次写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我国两大金融宏观监测与调控指标之一(另一大指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
《中国金融》是我发表有关社会融资规模文章的主要媒体之一,迄今已发表5篇以上,第一篇是发表于2011年第8期的《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最近一篇是发表于2025年第7期的《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看区域协调发展》。
在《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一文中,我指出,社融是我国金融理论和政策创新,同时也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可资借鉴。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整体流动性”理论,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理论。但由于这些理论并未成为西方货币政策的主流理论,同时西方国家也未在此基础上形成类似于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所以并不为大家所熟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对象不能仅限于商业银行或存款性金融机构,而应该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我国的社融指标应运而生。
《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看区域协调发展》一文阐述了社融蕴含着丰富的区域结构特征,能反映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别及发展趋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社融指标适合我国国情。我国中西部地区社融增量在全国的占比从2015年的38.6%上升为2024年的43.6%,涨幅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在全国占比小幅波动,平均为57.3%;东北地区则从2015年的7.0%降至2024年的1.2%。中西部地区社融增量占比上升,意味着金融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金融体系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增强。而东北振兴,则任重而道远。
利率、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需协调推进
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2012年,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相继在《中国金融》2012年第5期、第9期发表了《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研究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
第一篇报告指出,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不是完全放任跨境资本的自由兑换与流动,而是一种有管理的资本兑换与流动,是一个逐渐放松资本管制的过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资本账户开放的标准本身也在不断放宽。报告总结了国际经验,表明资本账户开放总体利大于弊。从我国实际看,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报告还提出优化资本账户开放路径,降低开放风险。
第二篇报告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应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分析了不可能三角理论、利率平价理论和所谓“先内后外”的金融改革次序论的局限性。报告接着总结了国际经验,表明金融改革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美国采用“先外后内”改革次序,依次实行本币国际化、放松资本管制、汇率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基本成功。尽管日本和韩国都基本遵循“先内后外”的改革次序,但日本并未能避免经济长期萧条,韩国经济也依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报告最后指出,我国各项金融改革是循序渐进、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的改革措施应该成熟一项、推进一项。
经过持续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形成了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到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利率体系。人民币汇率也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6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我国汇率制度归类为“软盯住汇率制度”中的“稳定化安排”,2020年6月将我国汇率制度进一步调整为“类似爬行的汇率安排”,2022年3月则将我国汇率制度归类为更接近浮动汇率制度的“其他管理安排”。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取得显著成效。直接投资项目下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证券投资已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开放格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较大步伐。截至2024年末,人民币位列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货币的比重已从过去的1%上升至2%左右。
由上可见,我国利率、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协调推进、相互促进,正在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金融内外平衡的体制、机制和调控框架,积极服务新发展格局。
虚拟货币本质上不是货币
《中国金融》2014年第7期发表了我和张璇合写的《虚拟货币本质上不是货币——以比特币为例》。此后,我在《中国金融》又发表了几篇剖析虚拟货币的文章。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这是货币的本质属性和最基本的职能,也是货币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鲜明标志。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自身必须能衡量商品的价值。在金本位制度下,人们通过黄金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价值由内在价值决定的金属货币体系发展为货币价值由国家信用支撑的现代信用体系,这就是国家发行的本位货币。本位币是一国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商品交换媒介,同时也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随着技术的进步,本位币由单一介质纸币发展为电子货币等多样介质,但货币的本质是不变的,即由国家信用支撑的流通手段。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首先是由于其缺乏国家信用支撑,难以作为本位货币履行商品交换媒介职能。虚拟货币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换取商品或完成支付,但能换取商品的并非都是货币。如,我国历史上的粮票、布票等都曾在较长时期、在很大范围内公开或半公开地能换取日用品,但从来没有人把粮票、布票定义为货币。货币成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基本条件是其普遍接受性。由于没有国家强制力支撑,虚拟货币的流通范围是很有限的,也是极不稳定的,很少有人把它们作为流通支付手段。
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自身价值不能剧烈波动。现代信用货币受国家货币当局的调控,自身价值不会剧烈波动,因而不可能被恶性炒作。而比特币则缺少本位币的这种中央调节机制,市值波动难以熨平;市值的剧烈波动又提供了巨大套利空间,进一步推动过度炒作,形成恶性循环。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币值的波动像比特币那样剧烈。2014年7月31日,比特币价格为582美元,一年后,下跌为284美元。2021年5月,比特币价格涨到5.9万美元,但到2022年12月,又回落到1.7万美元。截至2025年9月,比特币价格已经高达11万美元。如果以比特币计价,难以想象一件商品今天还价值100比特币,明天就变成200比特币了。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更多是虚拟资产,只是投资甚至投机的对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以上我举了三个方面的例子说明了我在《中国金融》发表文章的基本情况。此外,我在《中国金融》还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如2017年第10期发表的《我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与运用》、2020年第1期发表的《西方潜在产出理论离中国实践较远》。我也经常阅读其他作者在《中国金融》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般有三个特点:一是勇立中国金融改革潮头,研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二是有独到的见解,发人深省;三是符合国家经济金融的大政方针,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作出理论贡献。
感谢《中国金融》的同事们为我提供了发表理论研究成果的平台。祝愿《中国金融》再上层楼!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
作者盛松成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来源 | 《中国金融》2025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