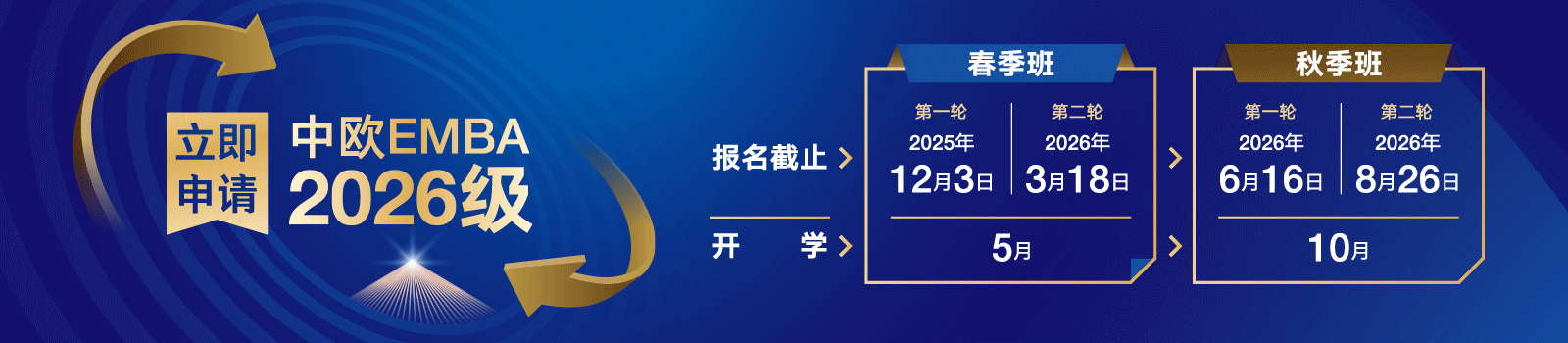高世名:人人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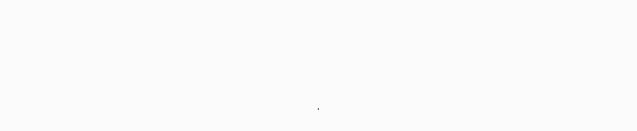
中国美术学院高世名做客中欧EMBA「人文艺术系列讲座」,从历史钩沉到当下的文学、音乐和电影,分享了自己的艺术观——「于人世琐碎中体味百感交集,于世事无常中披露万不得已,于常情常理中别开生面」。
● ● ●

高世名
中国美术学院
01/ 历史是一片汪洋
1919年,「留法三剑客」林风眠、林文铮、李金发乘上邮轮,前往法国。1924年,一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巴黎成立了「霍普斯画会」,也叫海外艺术运动社。
四年后,蔡元培先生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请林风眠担任校长,第一代教授群体就来自海外艺术运动社。中国美术学院的第一个校训:「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实际上是艺术运动社的宣言。
那一代人中,黄宾虹先生说「沟通欧亚,参澈唐宋,上追往古,下启来今」;林风眠先生要「从艺术运动出发,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建筑」;滕固先生说「我们要陶铸一个开物成务的时代,而使之绵延无极」。
这样一所学校,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赵无极是一个典范。他调和东西,在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基础上,把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现代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气息的新艺术。他的很多精神根底来自中国传统的意象、观物的方式,但他是现代的,能够被全世界接受。观众在读画的过程中,会激发起自己生命中的艺术时刻。那种远远的、隐隐约约、泥沙俱下的命运感,那种巨大的、无名的悲剧感,有时动荡不安,有时又有一种幽暗中的华丽。
黄宾虹先生是传统派的重要人物,被称作二十世纪传统派四大家之首。但他1948年在上海讲演结束时说:「未来的世界没有中国画和西洋画之分……让我们张开臂膀,等待着与一切来者握手。」这是什么样的胸襟?这样的胸襟,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历史观。
历史不是一条河流,更不是一条线性演进、持续向前的单向街。历史是一片汪洋,所谓「当代」只是暂时的海面,它是一个假象,海面下是无数的洋流动荡,纵横交错。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大师都在同一片历史的汪洋中载沉载浮;无论是荷马、柏拉图、孔夫子、苏格拉底、达芬奇,还是马远、夏圭、毕加索,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观念、一切形象、一切图式、一切手法,一切我们称之为风格要素的东西,也全都在这片汪洋之中。我们可以吸纳这些养分,打捞起所有的历史碎片,发展壮大自身。打捞起这些历史碎片是为了构造起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舟,法者如筏,我们还要发明一种彼岸,一个目的地,在这片浩瀚汪洋中开辟出自己新的航道。
对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创立者蔡元培先生来说,艺术意味着「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他在1928年4月8日的开学式上讲,创办国立艺术院就是要「以爱美的心唤醒人心,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他关心的是生活之建设。
同样是1928年,陶行知先生在湘湖之畔创办湘湖师范,培养乡村教师,他要推动的是平民教育,他的理想是「以四通八达之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一百年前,你几乎找不到第三个能跟蔡元培、陶行知媲美的伟大教育家。在20世纪的中国,他们都选择了杭州,他们创办的学校,一个往高处走,一个往下面扎,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士学」和「民学」。向上的路,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

02/ 艺术要有情有义
我们讨论艺术,希望艺术生发出新的感性,触达人类的悲欢,寄托心灵的探寻,能够让我们在新的人类状况中安身立命。
鲁迅先生的人物形象有一大部分是赵延年先生创造的。他从艺70年的时候我去看望他,问:「赵先生干了一辈子木刻,您图什么?」他说:「为了每一刀下去,都能够做到有情有义。」艺术要有情有义,艺术家要关乎情义。
黄宾虹先生画的梅花,老辣而又妩媚。中国画最牛的是什么?是这种完全相反的价值统合为一。中国画笔墨讲究「苍润」,苍中带润,既苍又润,愈苍愈润——苍是老辣,润是润泽,完全相反的东西相辅相成,聚合为一,就是中国画的特点。
我介绍现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两个人物。一位是2023年去世的万玛才旦。他拍《静静的嘛呢石》的时候,演员是个小喇嘛。小喇嘛后来还俗,娶妻生子,为生计奔波,经历了世俗中的人生。他先入戏,又出戏,在尘世中进入一场更大的戏,这一切都是完整的动人叙事。还俗的路是一条下山的路,然而这走向俗世尘埃的路途中所有的困扰和不得已,却使上山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是同一条路。
万玛才旦的故事从来不扣人心弦,而是平淡的、简单的、自然而然的,像野草在苍穹之下、大地之上静静生长、苍黄,周而复始。对万玛来说,生活就像水一样,那些过于精彩的故事像是形态各异的容器,人们总是聚焦在容器的形状和质地,但万玛希望我们去触摸水本身。他从来不把故事讲完,包括他人生的故事。他的心平气和、沉稳持重、克制与谦卑恰似草原上无声流淌的河流。光阴流转,青草生长,静水深流,这就是万玛的文学和电影。
第二位是黄永砯。他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切事件都是寓言般的存在,一切偶然都是机缘。他把每一次创作都视作参与世界历史隐秘链条的机会,黄永砯很早就意识到,一切重大事件都会迅速成为过去,只有艺术能让它留条尾巴,永无结局。只要事情没有结束,现实就保留开放性,历史就始终不会闭合,这是他的工作。
对黄永砯来说,现实已经预先准备好了作品的一半,他只是在完成另一半。所以世界是因,作品是果,果又生果,连绵不断;一切无常都是机缘,一切迷途都是迷津,因为迷即是津。他是一个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就像尼采一样。他说「艺术是一种危险的生活」,在他的墓碑上刻的就是这句话。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是「贵民」思想,所以在历朝历代都不受待见,我把他作为「民学」的起源。我看过刘震云写的《一句顶一万句》,非常感动,前年聘他做我们的客座教授。他的主题是百姓的精神生活,数不清的人,理不清的事,在书里满满当当但又空空落落。这些升斗小民在尘埃中的生命史,是他们生命力的意义与无意义,恩怨与寂寞,奈何与悲悯,超脱与羁绊。
文学艺术就是要于人世琐碎中体味百感交集,于世事无常中披露万不得已,于常情常理中别开生面。这三句话是我的艺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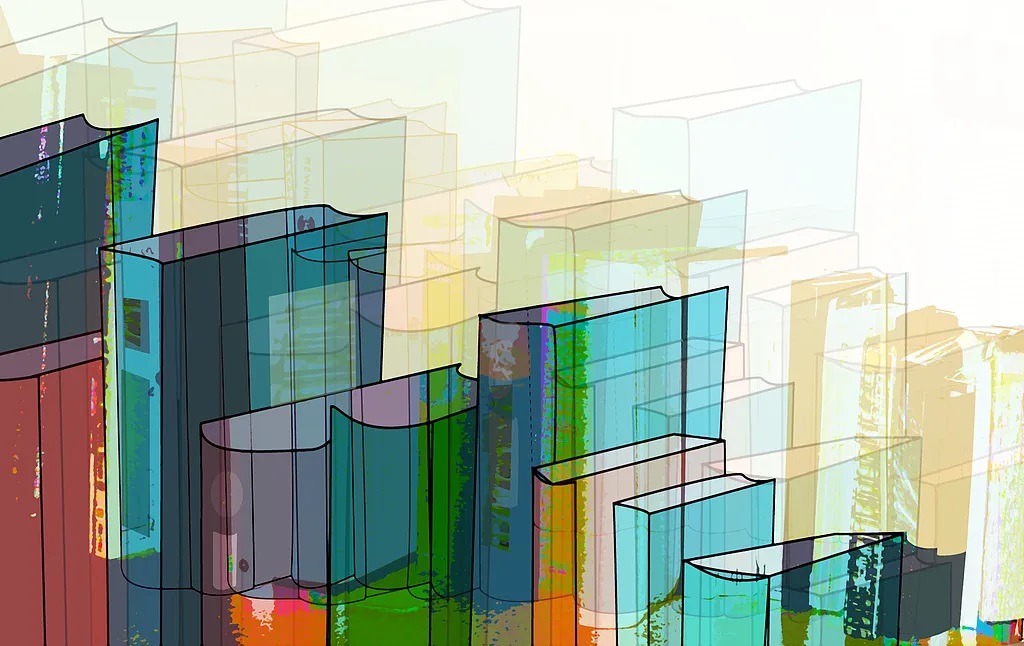
03/ 因创造而超越因艺术而通达
刀郎的新专辑——有一首《罗刹海市》可能大家都听过——他还为专辑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我看了之后非常尊敬。他说:「历史是人的历史,无论音乐还是文学都将回归到人、作品、时代,并以此回馈给未来的人们。」
听完刀郎的整个专辑你会发现,不通俗,编曲编得不通俗,歌词也不通俗。但是全球400多亿的播放量向我们证明了,文艺在这个时代是有力量的,因为艺术是诉诸感觉的,而感觉比知道更重要。他绝不是那类肤浅的「公知体」,在每一次反讽和批判的背后,还有一种通达与释然、惆怅与慈悲,这是艺术的人道主义。
书法家朱家济先生,前年我们出版了他的两大本书。最打动我的是他给母亲的上百通信札,用非常漂亮、流丽的行书和小楷写就。但他那时候是什么状态呢?60多岁的他正身处困苦磨难之间。
在极度困厄之中,他给母亲写的信依然是春风满纸,妙语连珠。他用轻松风趣的语调,俊拔流丽的书法,讲述劳动间歇的一次休憩、大会后简朴的餐食。田间劳作的苦、老疾俱致的苦、窘迫匮乏的苦,种种荒唐,无尽辛酸,在他笔下都化为生活的乐趣、人间的清欢,以告慰年迈的高堂。他信中轻松带过的那些点点滴滴,如果联系到朱家济先生当时的真实境遇,那是让人扼腕叹息,几度潸然泪下。
在古代,书法是日常之事。中国的书法史就是日常书写的历史,所有那些名家巨迹,没有一件是为了创作作品而写,都是日常书写。《黄州寒食帖》是诗稿;《争座位帖》是颜真卿告状的奏折;《祭侄文稿》是他的祭文草稿;《苦笋帖》是约饭的信札;《鸭头丸帖》是药方,据说治偏头疼……
这些书法经典,全部是在日常书写中随性而成,因情而就,妙手偶得。所以书法是身心一体的实践。「始转见性灵,点画为情致」指的是身心状态,它真实,瞒不了人,所以才说「字如其人,见字如面」。
但朱家济先生的信札却跟他的现实处境完全不同。一方面,他用轻松从容的笔调竭力掩饰自己每况愈下的现实处境,避免母亲的担忧。另一方面,这一通通远方的书信,一行行流丽绰约的书写,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一种生命仪式的转化?宛如旅途劳顿中的一抹霞光,是对现实苦难的创造性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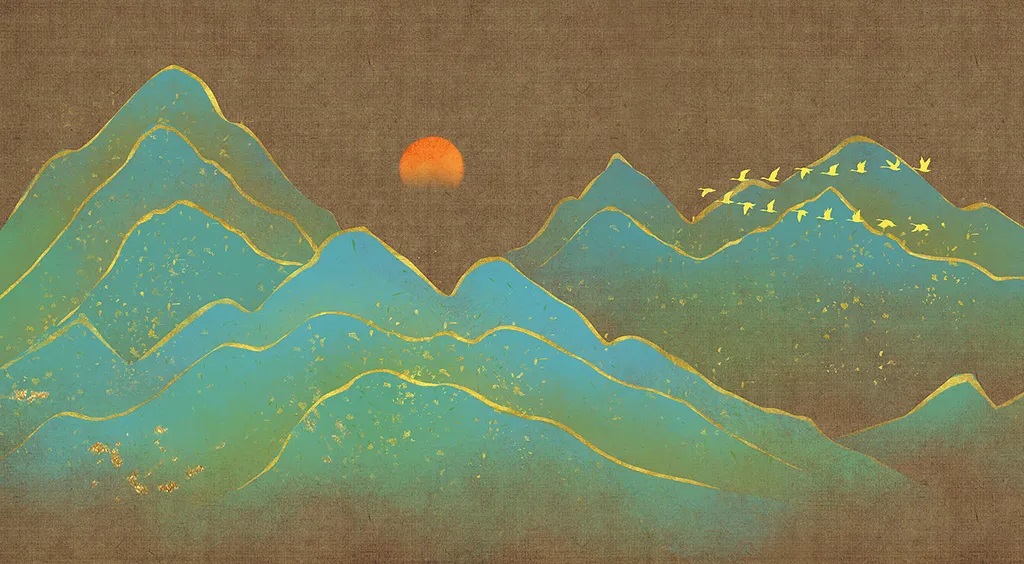
所以我说,没有艺术家,只有艺术时刻。艺术时刻,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这种创造性超越的时刻。这些涤荡心胸的故事,莫不标举出一份由艺术激荡出的磊落旷达,一种因创造而成就的精神超越。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如片玉珠尘般幽茫闪烁,映照出一肩明月、梦里山河,通达于中国文人的隐微情志,体现出艺术对于人生的深刻价值。
心灵因创造而超越,人生因艺术而通达。这就是我想分享的艺术时刻,不属于艺术家,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