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研社孙美林:坚守长期主义,做农夫,不做猎人
孙美林说“口袋有粮,心不慌”,融资资金将持续用于加强药物研发临床阶段的数字化等基础建设。本篇文章您即将看到药研社在这方面的所有心得。

以下根据药研社创始人兼CEO孙美林女士在中欧创业营九期第四模块上的分享《医药研发数字化的机遇与挑战》整理而成。
01/ 保安三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药研社目前有700多名全职员工,其中技术人员有200多人,所有团队都在上海,可谓是“技术重投入”。
但是我不是技术出身,也不是互联网出身,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试CTO,甚至我会在百度上搜“面试技术人员,应该问什么问题”。这样背景的我,每一次再融资的时候都会面对投资人的灵魂拷问:你怎么理解你的技术投入?
我觉得这要从“保安三问”开始讲起。创始人都是孤独的,需要做很多艰难的选择,需要长期的忍辱负重,更需要坚守。
我把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就比较坚定了,所以我每次做取舍的时候都特别快。他们都感叹说一个小小个子的女生怎么做判断的时候这么快,他们问你要不要商量商量?我说:不需要商量,我就能做主。
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要创业?好好的职业经理人不做,医生不做,在外企有很好的发展,曾经在这些大平台上的光环为什么要放弃,我为什么要折腾我自己?我觉得一个人的选择,其实底层逻辑上跟你的家庭背景、学识、价值观、世界观,都息息相关。

我在江苏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贫困,学了医也做过医生。对待弱势群体或者病患群体天生就是柔软的。所以我就想,虽然后来这些年没有继续再做医生,但我经历了药物研发行业后深深感受到这份职业的力量。
因为一个好药品的上市,它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甚至是几代人,可能比医生治病救人的能量价值还要大,也许正是这些因素,结合自身的经历让我有了创业的冲动。
真正开始做才发现,整个行业之低效,可以用“原始”来形容。大家知道药物研发在中国兴起不过20年的时间,最快速的发展就是最近的3~5年,在此之前中国一年也批不了几个创新药,所以几乎都是仿制药,连高仿都很少。
我在药厂、医院、研发机构都待过,我特别清楚患者面临的选择是极少的。所以基于这样一些背景,我在药物研发平台做高管的时候,自己就想怎么能把一个药物研发三年的周期缩短成两年半,可以提前上市,开始考虑很多产业底层的问题。
后来我自己创业其实是延续了这段经历,因为对行业的痛点体会深刻,所以我从一个公益的角度和源点创立了药研社。当然这一切的开始都要感谢我的先生,因为是他作为天使投资人支持了我的理想,让我有机会单纯的从一个行业公益的角度去出发。
创业前两年,我都没有想过这家公司应该怎么挣钱、挣谁的钱。产品能被行业内的人高效使用,我和团队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这本身就是创业的价值。
那么,从公益开始的药研社,为什么又突然在商业上有大的扩张?
其实“野心”是一步步被撑大的,跟着你的人多,你的责任就会多;你能做的事情越多,你看到的未来急需解决的问题就会越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在商业上没有任何变现,最后账面上只剩几十万块钱,还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其实要想做好公益,让更好更多的产品有条件被延续下去,除了激情之外,你还需要很好的商业变现能力。
另外,我觉得创业有很多的目标,但是一定会有共性,有时候兄弟给你的责任是最大的动力。
我创业这么多年唯一的一次失眠是2017年的某天晚上,因为白天我去了一位创业伙伴的家里看望他们的孩子,那一次我内心触动了,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跟随我的创业伙伴太苦了,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在上海这个偌大的城市,为了我们纯粹的理想大家一起创业,起初每个人只有几千元的生活费,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养家。
但是他们都从不抱怨,甚至我主动让他们出去找份高收入的工作先把家安顿好,但是他们却不走。那时候我很难过,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之前没有接受融资是因为我做的是一个公益项目,没有商业规划,我不知道如何给投资人回报。我一直是一个不愿意亏欠别人的人,所以我之前是拒绝资本的。

人多了,项目多了,流程和标准没有形成体系,集中爆发客户投诉,那时非常狼狈,对团队的打击很大,因为大家都非常有理想,想做个备受客户认可且信赖的企业。
给客户带去价值是我们骨子里都一致认同的价值观,但是事与愿违,我们在当时也没有逃脱传统行业的集中问题:客户投诉,不满意随处发生。
那个时候我思考很多,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把业务交付的过程,流程、管理等做到标准化,才有可能不仅仅是靠人的能力去解决问题,让符合能力的人进入到交付的过程中可以傻瓜化的操作就可以完成任务订单才是出路,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数字化这个词,当时我们整理说是供应链管理,其实也就是今天特别流行的数字化方式。
02/ 坚守长期主义,做农夫,不做猎人
1. 数字化是进行平台化的必经之路
数字化,全流程、全场景的数字化
平台化,从单纯的工具平台转换到真正的交易平台
智能化,AI驱动临研是非常好的趋势,但还需要时间
生态化,价值共生,共同发展
2. 坚守长期主义,做农夫,不做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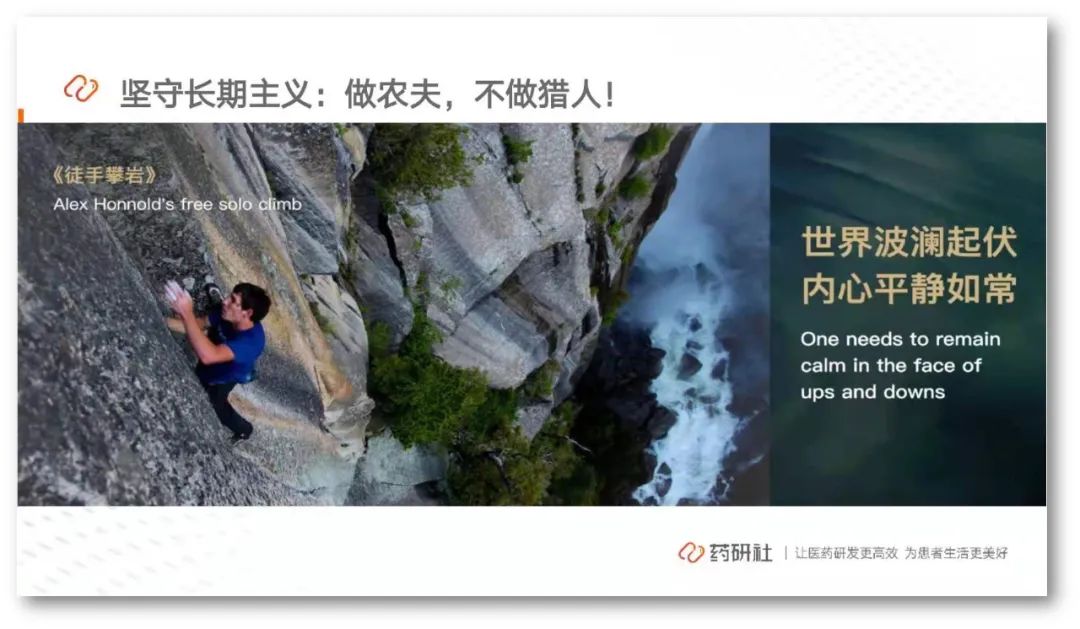
很多人都清楚数字化一定是趋势,可以解决很多效率的问题,但是为什么难做?为什么不愿意做?因为它的周期太长、繁琐,需要绝对专注,所以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一开始有这个想法以后,第一是定基调,我自己这么想,我得让我的团队怎么去匹配这样的定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公司现在所有的员工都知道我们要坚守长期主义,我们是农夫,不做猎人。
因为在最近两三年,整个医药市场非常火,火到无论有无Demo,都可以融到资;无论是否盈利,一上市市值都能达几百亿,面对这种现状如何让团队愿意坚守内心的理想,愿意全力以赴专注在当下的每个任务执行,是对团队非常大的挑战。
3. 三个法宝:团队+资本+定力
① 团队
我现在70%的时间都花在人身上,剩下的30%在战略规划上,其他的我不操心,因为的确伙伴还不错。
我在公司的两个组织担任组长,一个是文化发展小组,制定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以达到全员思想同频;一个是产品委员会,也就是数字化委员会,公司所有数字化产品构建的过程、规划等关键的讨论,我必须参与和主导决定。
在医疗这个高速扩张、并购与投资快速洗盘的赛道里,做好坚守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像一个传教士一样和团队时时刻刻去讲我们未来的大图是什么,通过这个大图,会留住很多跟你一样的人,也会淘汰一些不适合的人。
用使命愿景和文化价值观去留住团队,让大家不会轻易走散,是非常重要的。
② 资本
药研社做了很多轮融资,但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烧钱的公司,所以很多人都好奇:那你们为什么要融那么多钱?
因为我们深刻地明白:数字化对产业迭代是个长期大工程,你需要储备好资金才可以让时间成为优势而不是致命的挑战,如果你一边聚焦企业数字化,一边想着口袋里的银两是不是会随时断掉,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③ 定力
你以为今天跟大家同频一下,大家跟你喊一个口号就OK了,不是的,两三个月以后大家又开始怀疑自己了,所以很多事是企业1号位必须亲自去做的事情。
03/ 数字化过程中那些“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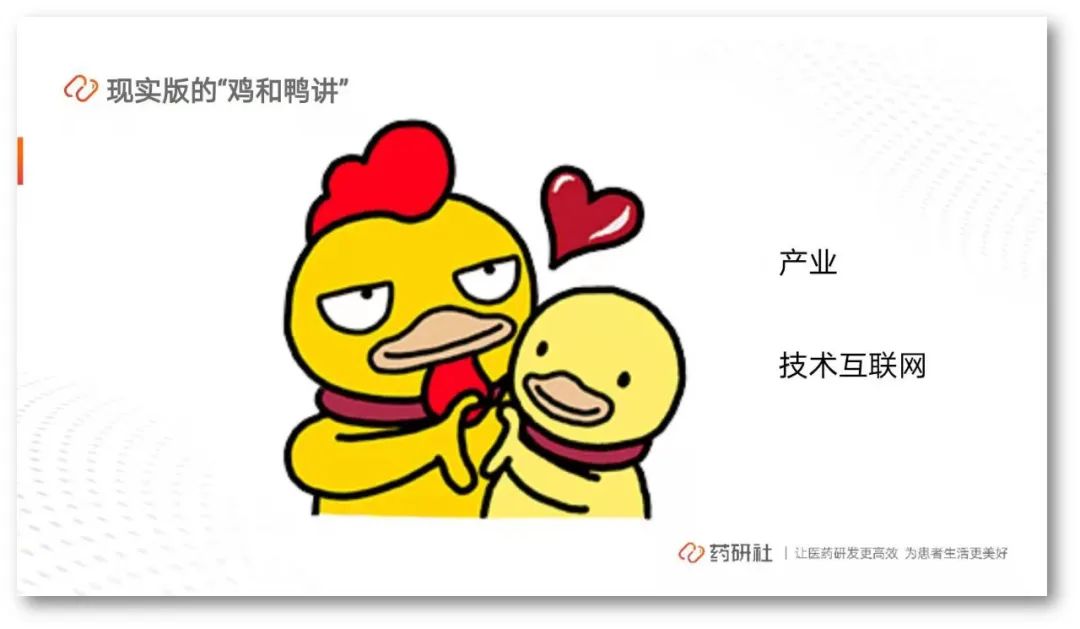
做研发的人是极其孤傲的,都是科学家思维,十分注重逻辑的严谨性。所以我的管理层自然形成两个梯队:一个是专家型,一个是互联网型。
我带着他们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三个穿牛仔衣过来的一定是IT团队,穿西装来的一定是医疗团队,当中经历了太多“鸡同鸭讲”的过程,因为没有围绕业务场景来做。
吵架吵了半年,到底谁先融入谁?我最后找到了一个好方法,毕竟患者的心态其实是每个人都感受过的:不舒服、无助、无奈、等待、排队等等,对医生甚至充满不信任,对此大家都感同身受。最后想了一个办法,所有人必须以业务场景来说话,不在业务场景里说的话都不是人话。
2. 思想同频,走出去,请进来。
我们这个行业目前做数字化还没有成功案例,所以我们只能跨行业去看,就去参观贝壳。卖房子的场景比我们医疗的场景要复杂得多,但是贝壳却能把数字楼盘字典做得那么扎实,每一个分工流程那么优秀、顺畅,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有时候看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所以这对我们的员工很有启发,我们说战略的共识是走出去,请进来,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目前数字化三年的时间,一开始我们就像难产一样,肚子大,生不出来。到现在生出来、走下去、投入应用。以前开月度高管会要花一天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低效汇报各种信息。现在我们开会两个小时解决,因为我们都有仪表盘,所有的数据全部在线化,每天打开电脑看一下,哪个地方亮红灯了需要关注一下,通过数据完全可以分析出来。

04/ 最后一步是1号位工程
疫情的爆发,对整个远程医疗、远程临床研发做了非常好的市场教育,所以药研社也做了软硬件结合,为未来三年以后的竞争做准备。比如是不是很多的疾病的研究可以居家做?其实物理条件也够了,网络条件也够了,人的意识也够了,就是在场景上,谁连通的早谁就更有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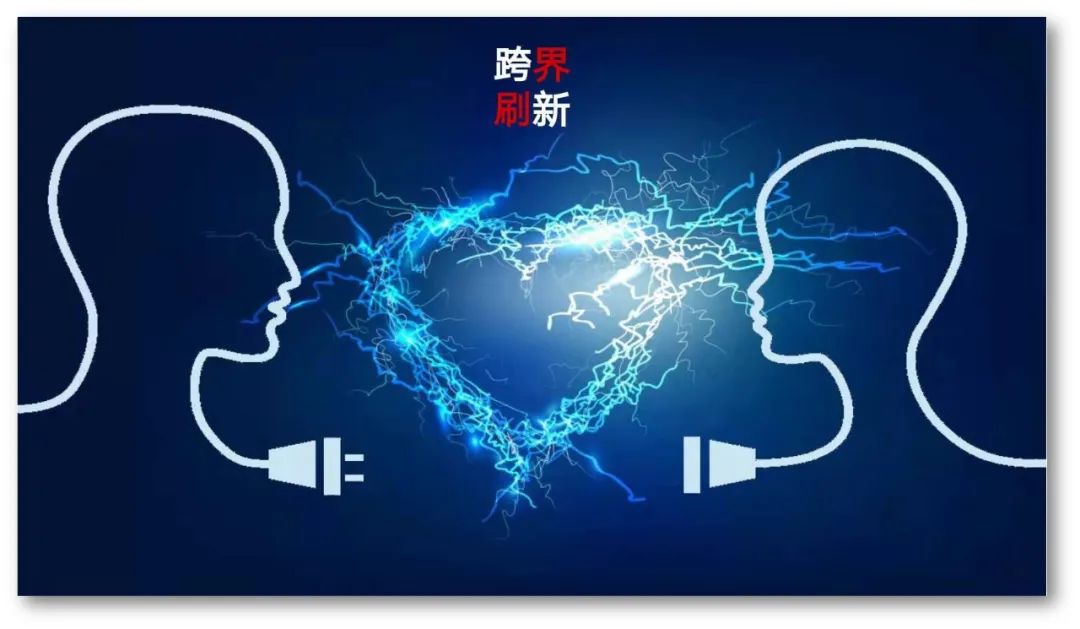
如果心中没有那个“大图”,如果没有商业理想,一路全是诱惑和挑战,很难去坚守。
05/ 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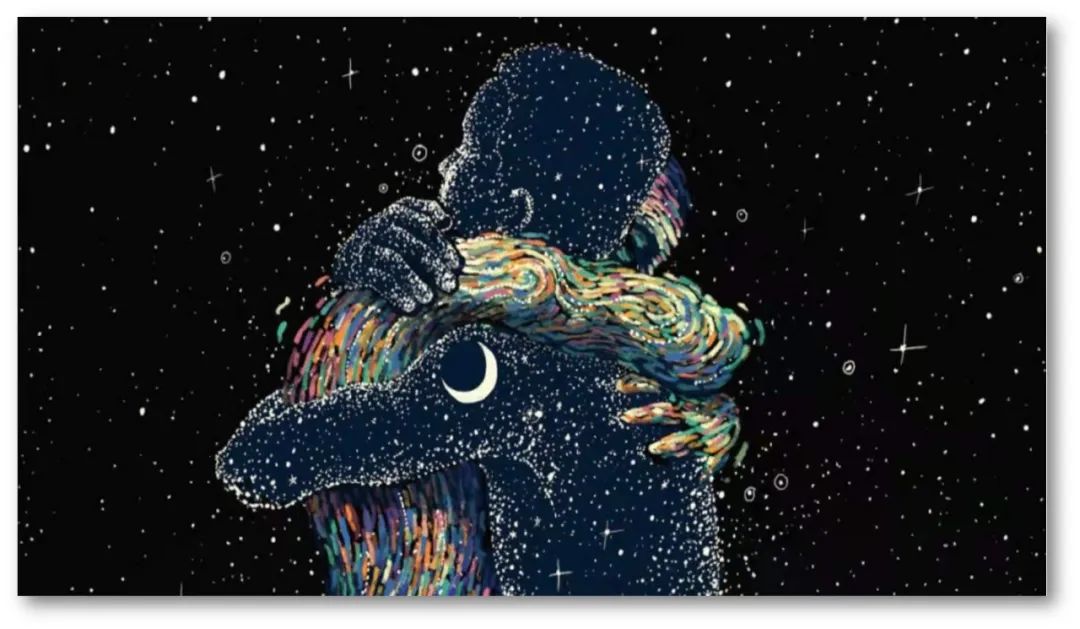
创业营这几年的招生主题都是“产业深耕、产业再造”,我特别理解这八个字其中的酸甜。我特别坚信,产业和技术的终极就像这幅图一样美,会有很多可想象的空间,我觉得现在很多产业都值得用数字化的方式重新再做一遍,看似没有机会的方向,仔细分析,还是有很多价值,谢谢大家。




















